杀人者与被杀者的一步之距
June 12, 2011 on 10:45 pm | In 书斋札记 | No Comments提起拉美文学,首先想到的是瑰丽奇想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特·富恩特斯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巨匠。不过近年来,一批新生代的拉美作家正在崛起,随着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多的被译成英语,他们的成绩日益受到国际文坛的瞩目。
2007年夏,三十九位三十九岁以下的南美作家组成了一个名为“波哥大39”的文学团体,成员有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布里埃尔·瓦斯克斯(Juan Gabriel Vazquez)、用英语创作的秘鲁裔作家丹尼尔·阿拉尔孔(Daniel Alarcon)、出生在多米尼加、以《奥斯卡·瓦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普利策小说奖的朱诺·迪亚斯等。
是什么初衷让这些作家走到一起?加布里埃尔·瓦斯克斯解释说,“原因很简单──拉美文学爆炸(的辉煌成就)削弱了后一代人的创作声音。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为后继者打开了大门,但他们那一代的才华和影响如此巨大,完全主宰了欧洲人对南美文学的先入之见。现在,我们这代孙子辈的作家,从他们身上获益,但不再走在他们的阴影下。”透过他们的作品,如加布里埃尔·瓦斯克斯的《告密者》(The Informers)和阿拉尔孔的短篇集《烛光下的战争》(War by Candlelight),可以发现,离开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采用鲜明的写实手法是这一代年轻拉美作家创作的一大特点,而刚获得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秘鲁作家圣地亚哥·郎卡格里奥罗(Santiago Roncagliolo)的长篇小说《红四月》(Red April)亦属其中之列。
承载着黑暗沉重历史的惊悚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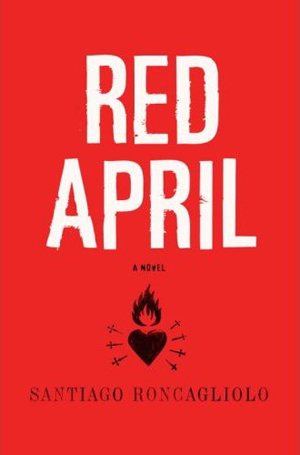 有记者问郎卡格里奥罗,《红四月》是政治小说还是惊悚小说?郎卡格里奥罗回答:“都是,取决于读者是谁。对拉美地区的读者而言,居首位的是政治暴力。在欧洲,人们把它当作惊悚小说来读。我觉得那样挺好。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去省思政治语境下的暴力。”
有记者问郎卡格里奥罗,《红四月》是政治小说还是惊悚小说?郎卡格里奥罗回答:“都是,取决于读者是谁。对拉美地区的读者而言,居首位的是政治暴力。在欧洲,人们把它当作惊悚小说来读。我觉得那样挺好。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去省思政治语境下的暴力。”
郎卡格里奥罗的父亲是位政治学家,七十年代因与军人政府的关系紧张而短暂流亡墨西哥,郎卡格里奥罗从很小时候就体会到拉美动荡的政局与流离失所的飘零感。在极左毛派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的势力处于末期的九十年代,他参与了秘鲁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从中了解到许多反抗者与政府间对峙交火、屠戮平民的野蛮行径。《红四月》正是一部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小说。
主人公菲力克斯·查卡尔塔纳·萨尔迪瓦(Felix Chacaltana Saldivar)是一位自愿申请从首都利马调回家乡阿亚库乔(Ayacucho)的检察官。故事发生在2000年,历时二十年的内战已正式宣告结束。四月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是天主教重要的宗教节日圣周节,来自世界各地及秘鲁国内的游客,将从利马涌入南部安第斯山区的阿亚库乔,观摩参加这座城市著名的圣周节游行。在庆祝活动开始前夕,城里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正直“迂腐”的检察官查卡尔塔纳不遗余力的想追查真相,但当地警察消极不配合,司法人员只想着升迁调职,对查案敷衍懈怠,官场的腐败昭然若揭。然而,天真的查卡尔塔纳非但没有洞悉这层黑幕,还不识时务的一味坚持自己的理念,他书呆子似的执著显得可笑又可悲。作者郎卡格里奥罗坦承,查卡尔塔纳身上不乏有自己在人权委员会工作时的影子──一个“自以为可以依法办事、维持秩序的荒诞的小人物”。
查卡尔塔纳相信杀人焚尸与“光辉道路”组织的恐怖活动有关,但为避免恐慌、保证圣周节庆典的顺利举行,欲盖弥彰的军方头目朝他吼道,“在这个国家里没有恐怖主义,这是上级的命令。”可在圣周节期间,不仅又有接二连三的死者出现,而且极端凶残的杀人手法与现场留下的“光辉道路”的口号及签名,似乎佐证了查卡尔塔纳的推测,更巧合的是,所有死者都是他私下调查中接触过的人。
《红四月》以纪实性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悬疑丛生的故事。曲折意外的结局,不仅牵扯出险恶诡谲的政治阴谋,还勾起查卡尔塔纳一段隐秘的童年往事。凶手变成下一个死者,受害者变成凶手,小说描绘了暴力循环的困境,探讨“善良与邪恶之间那条薄弱的红线”,对以任何名义实施暴行的正当性提出质疑。郎卡格里奥罗说,“在秘鲁(也在西班牙),人们都在反思暴力的过去,寻找新的理解途经。我们是秘鲁第一批以内战为主题、但并未参加过战争的作者,我们写作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时代。二十世纪比较简单:不是共产主义者,就是资本主义者。但对我们这一代而言,柏林墙倒了,接着是华尔街……”
“有文学的地方就有翻译”
英国的《独立报》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创立于1990年,奖励每前一年在英国出版的英语翻译小说,中间中断过五年(1996─2001)。这个文学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颁给作者与译者,由双方平分奖金。在英语文坛普遍不重视翻译、译者常常成为“隐形人”的现状下,该奖对译者的肯定显得尤为可贵。历年的获奖作有奥罕·帕慕克早期的小说《白色城堡》、米兰·昆德拉的《不朽》、何塞·萨拉马戈的《里卡多‧雷伊斯的死亡之年》(The year of the death of Ricardo Reis)、佩尔·帕特森的《外出偷马》等,中国作家郭小橹的《石头村》、毕飞宇的《青衣》也都曾入围过。
入围今年短名单的作家作品格外耀眼,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有获过IMPAC都柏林文学奖的帕特森的《咒逝川》(I Curse the River of Time),但最后,评委们一致决定将奖授予目前定居在巴塞罗那的秘鲁作家圣地亚哥·郎卡格里奥罗,称赞他的《红四月》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将娴熟的叙事技巧、心理剧与揭露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的小说,这也使三十六岁的郎卡格里奥罗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既然这是一个难得同时肯定作者和译者成绩的文学奖项,因此不能不提到《红四月》的英语译者伊迪丝·格罗斯曼(Edith Grossman)。年逾七旬的格罗斯曼是一位荣获过多个文学翻译奖的美国译者,2003年由她翻译的新的《堂吉诃德》英译本,得到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与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赞誉。圣地亚哥·郎卡格里奥罗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很喜欢格罗斯曼翻译的《红四月》,“在这本书里,难点之一是怎么译出没文化的官员想要表现得有文化而常常使用的那种令人发噱的官腔语言。”
伊迪丝·格罗斯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西班牙语─英语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亦有深刻的洞见。在去年出版的《翻译为什么重要》(Why Translation Matters,耶鲁大学系列讲座之一)一书中,格罗斯曼从文学史的角度,为翻译的原创性正名。她指出,将译作置于原作阴影下、质疑其原创性,是浪漫主义运动倡导个人主义、强调狭义的独创性而遗留下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人会因为译者不是第一作者而小看他们,相反,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翻译。大量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的宗教书籍和经典作品被译成欧洲现代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文艺复兴也可称作是个“翻译的时代”。
针对英语出版界对译介非英语作品的冷淡态度,格罗斯曼以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例,说明不同语言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和相互成就,论述文学翻译的必要性。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时读了被译成西班牙语的福克纳的小说,受到他神话式、大历史、多代人的叙事视野的影响,创作了《百年孤独》等多本传世杰作,反过来,这些作品日后也影响了托尼·莫里森、萨尔曼·拉什迪、唐·德里罗、迈克尔·查邦等多位当代英语作家。促成这一文学对话与互动的正是翻译。“翻译具有一股强大的渗透力,它使人有机会走入不单只局限于一国或一种语言传统的文学世界,从而拓展和深化作者对文体、技巧和结构的领悟力。”虽然在引进外国作品方面,中文出版界与英语出版界的冷热程度大相径庭,但格罗斯曼对翻译的真知灼见,同样值得人思考。
(for《上海壹周》)
No Comments yet »
RSS feed for comments on this post.
Leave a comment
Powered by WordPress with theme based on Pool theme design by Borja Fernandez.
Entries and comments feeds.
Valid XHTML and CSS.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