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McGurl: The Program Era
December 2, 2009 on 11:53 am | In 书斋札记 | 2 Comment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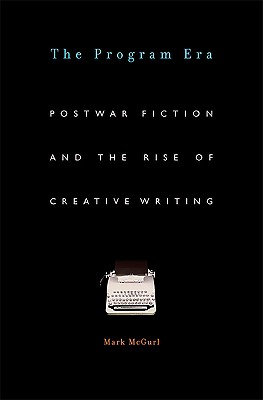 创意写作与美国战后文学
创意写作与美国战后文学
──《系统时代:美国战后小说及创意写作的兴起》马克·麦格尔 著(The Program Era: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 Mark McGurl)
初识保罗·安格尔是在聂华苓女士的文章里。他是诗人、作家,但在美国文学界,他最引人瞩目、最为人铭记的,也许不在于他的作品,而是他曾担任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的系主任。在二十四年的任期内(1941─1965),他吸引优秀作家到爱荷华任教、扩大招生规模、录取有潜质的学生,使创意写作成为一门新兴科目在美国大学内得以确立和推广。
创意写作项目,英语叫作Creative Writing Program,和汉堡一样,是地道的美国原装货。不同于一般大学课程、由学识渊博的教授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思维方法,创意写作的教学比较接近集体工作室的运作方式,十几个学生与老师组成一个合作团体,每个学生在课上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由其他人各抒已见,优点、缺点、称赞、批评、修改意见……老师作为中介人,负责控制调节讨论的节奏,确保不偏离主题,也发表个人看法,但不是从权威者的角度。因此,《纽约客》作者露易丝·曼南德(Louis Menand)把创意写作的教学理念概括为:“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能够教会另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如何写出一首能被发表的诗歌”。从1936年爱荷华大学成立的第一个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发展至今,全美目前有822个创意写作班,153个授予艺术硕士学位(Master of Fine Arts)的创意写作项目,其中37个还颁给博士学位。和大多数研究院的专业一样,许多名校的创意写作系也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
创意写作项目在美国校园遍地开花,纵观二战后美国文坛,一大批作家都能与写作班扯上关系,弗兰纳里·奥康纳、库尔特·冯内古特、菲利普·罗斯、托尼·莫瑞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Tobias Wolff、Larry McMurtry、Marilynne Robinson、Elizabeth Strout、Jhumpa Lahiri、David Foster Wallace……他们或曾是写作班的学生,或是写作系的教授,或从学生变为教授,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列很长,甚至跨过大西洋,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创立了英国第一个授予硕士学位的创意写作项目,而布克奖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然而,写作毕竟是一项凭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活动,没有既定的规则规律可循,真的可以教得会吗?对此,连有些在写作班任教的作家也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即使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也在主页上这么写道,“我们相信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作家是可以被鼓励(成才)的。”走出过16位普利策获奖作家和无数文学奖获奖作者,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没有把这些辉煌归功于自己成功的教学,反而表示,这些才华洋溢的诗人、小说家、短篇故事作家带给写作班的,比他们从写作班里得到的更多。
有关写作能不能教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对创意写作项目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但都没能阻挡它蓬勃发展的势头。据调查,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墨西哥、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纷纷开始效仿美国,在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因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英语系教授马克·麦格尔提出,无论对写作班存在多少无可厚非的争议,现在是时候把它当作一个既定现象和事实,进行历史的分析与阐释:产生的经过、原因、引致的结果。《系统时代:美国战后小说及创意写作的兴起》(The Program Era: 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便是第一本系统梳理、分析、论述创意写作的研究著作。
创意写作的兴起及大热与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空前繁荣有紧密联系。60年代,美国高校数目急遽增加,主要集中在公立院校的建立,势头最旺时,平均一周便有一所社区大学诞生。对院校而言,提升学术形象的一个重要途经是增加授予学位的专业科目,写作班便在这股大潮中,越来越多的成为授予艺术学位的创意写作系。
写作班大热的另一个原因与战后美国政府的助学政策有关。书中特别提到“美国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 of Rights),该法案旨在向二战退伍军人提供教育补助,引发了一股高校入学潮,很多人选择了不需特别专业背景的写作班。课上,他们把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见闻述诸笔端,这些独特的个人叙述,反过来吸引了专业作家的注意。在斯坦福任教的华莱士·斯泰格纳被班上一个退伍学生写的故事深深打动。他发现,他们“有很多可写的故事,但他们结了婚,有的有小孩……他们需要一个像咖啡馆一样的地方,讨论、创作”。于是,斯泰格纳把这个想法成功“卖”给了某石油大亨,由他出资,在斯坦福开设了创意写作系。此外,因为法案规定,接受资助的人必须选读颁发学位或证书的专业,这反过来也促使了写作班上升为一个颁发学位的科系。
创意写作集中体现了美国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的主张。一方面,从实践中学习,打破了“作家天生”的成见,通过让学生参与,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好奇心,发掘创造力。写作班像一个学徒工作室,每人交出自己的作品,任一群陌生人对它指手划脚、把它批得体无全肤,麦格尔形容这是个公开接受羞辱的残酷过程,目的是为把今天丢人的烂作改造完善成将来令人骄傲的出版物。另一方面,进步教育强调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自我表达机会,这恰是创意写作教学的一个核心。每个写作班的老师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写你知道的”。不断从个人的经历、回忆、观察、思考中深挖素材,写出以往没人写过的原创作品。写作,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用写作完成个人体验。麦格尔将之视为反身性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表现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个标志。
自我表达的另一个特点是找到自己的“声音”,这对少数裔和女性作家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的书写有时代表的不只是个人,还被当作沉默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写作班提供了一个平台和通道,使被忽略的声音在公共领域得到倾听。创意写作的发展既与美国多元文化的深厚传统不无关系,反过来又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多样性。比如,60年代美国非裔作家开创的新奴隶文学(neo-slave narrative,其中最著名的是托尼·莫瑞森的《宠儿》),问世的第一部作品《禧年》(Jubilee),乃是作者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在爱荷华写作系的博士毕业作。
不过,从美国大学走出来的少数裔作家,其作品能否坚持自身文化的纯正性,遭到一些文学教授的质疑。麦格尔在书中举印第安作家斯科特·莫马迪(Scott Momaday)的《黎明之屋》(House Made of Dawn)为例,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印第安文学的教授Karl Kroeber 批评这部作品的叙事美学完全是英美文学的套路,根本有违印第安文学的传统。麦格尔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莫马迪既然是个印第安裔作家,其创作受白人现代文学的影响,应被视为一种吸收,不是污染,表明现代性走入印第安艺术,成为其中一个因子。
当代作家与大学的关系日益密切,许多作家拥有大学学位,不乏硕士博士,不少在大学任教,人们把他们统称为象牙塔里的作者。他们可能缺乏广阔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创作可能曲高和寡,这样的作品,如何吸引读者?针对这一怀疑,麦格尔指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训练出了一个精英读者群体,他们正是这些阳春白雪作品的欣赏者和消费者。50年代以来兴盛的校园小说(campus novel),便是高等教育扩张体现在文学上的一个例子。著名的校园小说包括有玛丽·麦卡锡的《学界丛林》(The Groves of Academe)、纳博科夫的《普宁》(Pnin)、Philip Roth的《人性的污点》(The Human Stain)和《愤怒》(Indignation)、库切的《耻》(Disgrace)等。因此,写作班非但没有使作者脱离生活,反而把他们引入大学这块孕育和消化文学小说的富饶土壤,与读者建立起最亲密的接触。更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将来又可能成为大学文学系研究的对象。从读者、作者到研究者,创意写作项目无形中创造了一条象牙塔里自给自足的食物链,是个不能不引起人注意的屌诡现象。
学院式的训练是否会伤害艺术创作的自由个性,为何要把私人写作纳入制度化的学院体系,支持者如保罗·安格尔等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给予作家经济上的支持或尊重太少,大学不得不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份资助和保护文学创作的责任。至今,创意写作项目为许多本只能依靠写作或研究基金为生的作家提供了一份有固定薪水的教职。而麦格尔认为,除了经济原因,创意写作产生于美国大学的更深层因素,包含了一种企图同时追求自我表现(self-expressive)与实现自律(self-disciplined)的悖论,他将之概括为“制度下的个性化”(institutionalizing individuality)。
反对者抨击大学写作班不是在培养作家、而是批量制造无个性的写作机器,并把文学的衰落、大师级作家的缺失归咎于此。麦格尔驳斥这些非议属于背离时代、固执守旧的偏见。大众高等教育的普及,使精英人才不再是金字塔尖的稀有物,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而写作班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所谓没有大师,绝非表示现在的作家都是平庸之辈,而是因为整体水平的提高,要在今日文坛鹤立鸡群,比莎士比亚时代显然困难得多。而且,谁也无法否认,美国战后小说取得的成就、涌现的优秀作品,超过了战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与创意写作项目带动的集体努力密不可分;因此,即使文学真得将死,也决不是项目本身的过错。
创意写作不会把文学引向穷途,但写作究竟能不能教,仍旧是众说纷纭、盘绕人们心中的最大疑问。如果写作不是一门手把手能教会的技艺或学问,方兴未艾的写作班对文学创作有何意义?近年来屡获文学奖项、被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美国杰出青年小说家的华人女作家李翊云,曾就读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目前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创意写作。在一次采访中,我向她提出这个疑问。她的回答,或许能解开几分疑惑。
作为学生,你在爱荷华写作班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李翊云:“去学写作,有两个目的,一是结识写作上的朋友,像我一些最好的朋友,都是写作班时的同学,他们会陪伴你一辈子的写作生涯,这种友谊很可贵。我们在一起不聊别的,就讨论书。第二,在写作班学的其实不是写作,而是怎么读书,跟着那些教授会发现自己原来的读书可能并不得法。另外,我也是在念写作班时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文学偶像──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这个很重要。具体写作技巧相对是次要的。”
角色转换,成为老师,你在教授写作时,主要教给学生什么?
李翊云:“我会教他们一些写作技巧上的窍门和捷径,但光凭这些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我无法教他们怎么写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但能指出他们习作的毛病,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写不对。另外,我会和他们分享我认为好的作家,教他们怎么读文学作品。”
(《书城》12月号)
2 Comments »
RSS feed for comments on this post.
Leave a comment
Powered by WordPress with theme based on Pool theme design by Borja Fernandez.
Entries and comments feeds.
Valid XHTML and CSS. ^Top^
这本书也有中文版了。总感觉光凭写作教写作是教不好的,就像李翊云自己也没办法告诉学生大师的作品该是什么样。我总觉得,作家应学得尽可能的多,说作家不是思想家是苛刻的,但必须承认,作为读者那些思想家作家才会带给他们最深的感动。
Comment by lmzlh — December 24, 2011 12:33 am GMT-0700 #
当代普遍水平确实比以前要高,随着教育的普及。但全景式的作家不再可能有了。虽然会有在小说里放置很多东西的作家,但真实感没有了。全景式不在于物理上涉及内容的多寡,而是是否写出作家生活里最广最深的成分。或者说,不在于写的是否是宇宙,而在于能否将自己的生活写出宇宙感。
Comment by lmzlh — December 24, 2011 12:40 am GMT-0700 #